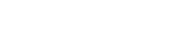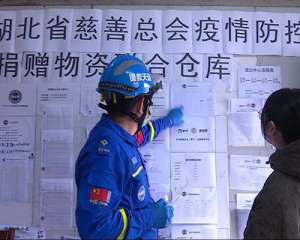灵秀在上观 文
阳春三月,桃红柳绿,上观桃园小镇游人如织,梨树沟文化节大舞台前,热热闹闹的原始农耕文化表演如火如荼:挥鞭深耕的庄稼汉,吭哧吭哧耙地的壮小伙,摇耧种地的老农,施肥松土的村妇,锄头翻飞,簸箕轻扬,磨盘流转,牛铃叮当,老农挥汗如雨,村姑汗流浃背,好一幅热火朝天的农耕生活图!
远道而来的观众,伸颈、侧目、微笑、默叹:曾经的农耕、农村、农民,没有旋耕机,没有播种机,世世代代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......科技一日千里,农村日新月异。
在当地文化站刘站长的陪同下,我们“灵秀师苑风”一行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,一路欣赏漫山遍野的桃花。
这是花的世界,这是花的海洋,妖娆烂漫,千媚百娇。这些可爱的精灵们,各施手段,竟弄身姿,攀于枝头:或正、或侧、或仰、或俯,有的粉如荷,有的凝如脂,花或绽放,或半开,偶然会碰到几支懒起的,羞得小脸通红。
花丛中,老人欢笑,孩子嬉戏,年轻人忙着拍照。生活真像花儿一样。
风景这边独好!我一边慨叹,一边和刘站长攀谈:
上观原属豫西深山区,土地贫瘠,十年九旱:山上没有参天的乔木,少有丛生的灌木,有的地方甚至寸草不生,裸露的黄土,凸起的岩石,像癞痢头上稀疏的黄毛,疏疏落落生长着几束荒草,几丛荆棘,荒山野岭,地瘠民贫,历任乡干部一分到这兔子都不愿拉屎的地方,都觉得像遭流放一般委屈。
几年前,村村通公路修成,村民霍敬虔动上脑筋,他辗转买了一批水蜜桃树苗,种在自家的责任田,栉风沐雨,辛勤劳作,一举成名。村民跃跃欲试。
以赵利勋和张明明为首的乡领导从中看出门道,看出希望,他们一边号召村民大规模种植水蜜桃,以形成气候,一边利用各种媒体宣传、推出上观桃园小镇,并实施农产品、土特产,生产、加工、销售一条龙服务,连续四年举办声势浩大的桃桃园文化节活动。
游人来了,客商来了,机遇来了,上观桃园小镇的春天来了!
不知不觉间,我们来到上观闻名的一棵景观树一一千年抱榆前,但见树身不足两米高,虬枝嶙峋,旁逸斜出,佝偻的身子,侏儒般蜷曲,唯一的一只手臂却横空伸展,枝繁叶茂,树身上一条条用来祈福的红布条随风翻飞,流苏般美丽,一串串嫩黄的榆钱,诱惑着游人。
我的思绪一下子穿越时空: 遥想当年,其貌不扬,甚至畸形生长的榆树何其沮丧:要才没才,要貌没貌,自惭形秽地站在一脉溪流旁,望眼欲穿,一等千年。它的兄弟姐妹都成梁、成椽,甚至成柴,可鸟儿不屑在它身边栖息,就连樵夫都懒得看上它一眼。
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。沉寂千年,老榆树竟然活成了神仙!活成了方圆百里村民的福祉!时也?运也?千年抱榆在春风里发出浩叹!
中午,“灵秀”一行人在一农家乐饭庄吃饭:劲道的手擀红薯面条,黄灿灿的炒鸡蛋,喷香的油煎小蒜沫儿,青灵灵的山野菜,早勾起我们肚子里的馋虫,吃了一碗又一碗。老板娘见我们盛赞她的手艺,话匣子一下子打开:
俺俩男娃,大娃在路边开个山货收购批发店,媳妇儿收摊儿,大娃采购、送货,孙子、孙女都在县城幼儿园寄宿。老二在郑大念书,说是毕业了,要帮我把手擀红薯面搬到省城开连锁店!
我们一行人都夸大娘好福气。
大娘笑了: 不瞒你说,俺家前几年有多穷!大娃连媳妇都讨不上,倒插门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。不成想这两年俺桃园小镇火了,光俺的小店一年净挣十来万!大娃和媳妇一合计,干脆搬回来住,在路边开了个商店,生意红火哩。老二也争气,一下子考进郑州大学!领通知书那天,书记,乡长敲锣打鼓送来一万元学费。 我呀,成天想着:这天上掉下馅饼的好事儿,咋叫俺碰上了!俺咋镇幸运!
是的,桃园小镇的村民真幸运:以前只知道金针、木耳能卖钱,谁知道野山药、葛根更值钱;光知道灵芝、毛栗子能换钱,谁成想何首乌、花生酱更能赚大钱;野菜、小蒜、玉米糁儿,连门前的花花草草都是成城里人的宝贝疙瘩;自家种的樱桃、水蜜桃、萝卜、白菜,人家城里人拖儿带女帮咱摘、挖,工钱不要,反过来还把整过的东西掏高价买走!
淳朴的桃园乡亲,再用不着捧着金碗去讨饭!
人说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问题是靠的支点在哪里,吃的方式是什么?
看来,扬汤止沸,不如釜底抽薪。
看来,扶贫扶志,不如扶贫扶智。
看来,灵秀在上观,是因为领袖在上观。
作者简介
灵秀师苑风编委
朗读者简介
江岩,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,喜欢音乐、文学。江岩,江边的一块岩石,无论风吹雨打,都会在那里巍然屹立,细细品味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笑看人生的风云变幻!